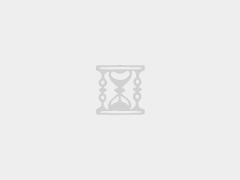白银悲剧发生后这一年,国内大型越野跑赛事显著减少。图为2021年底,巴图鲁勇士山地户外运动挑战赛在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东升农场举行。(视觉中国/图)
白银悲剧发生后这一年,国内大型越野跑赛事显著减少。图为2021年底,巴图鲁勇士山地户外运动挑战赛在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东升农场举行。(视觉中国/图)
最初,许多跑者承认,与越野赛结缘更像个意外。11年前,退役的河北省体工大队障碍跑运动员顾冰突发奇想,第一次跑上居庸关。尽管时常抱怨牛刀初试时的疲惫——第一次上百公里的越野跑下来,他掉了9个脚指甲,浑身无力,半个月内都动弹不得,但在恢复后,他又想再次奔赴赛道。
渐渐地,他与越野跑再难分开了。对于顾冰而言,越野跑是饭碗,也是爱好。
11年间,越来越多的职业或非职业跑者涌向山林。越野跑赛事也从早期的一年十几场,发展到一年数百场。穿过崇礼的寒风,踏过瓜州的流沙,翻过秦岭的隘口……越野跑的赛道延伸到哪里,跑者们的足迹就印在哪里。
直到在甘肃白银的戈壁,它重重地摔了一跤。
2021年5月22日,黄河石林山地马拉松百公里越野赛在强度难度最高赛段遭遇大风、降水、降温的高影响天气,造成21名参赛选手因急性失温死亡。
一年来,恐惧始终萦绕在幸存者许滢初心头,即便鼓起勇气重新跑入山林,她也总会想起那绵延在光秃秃石林之中的恶寒。顾冰没有参加白银越野赛,但好友梁晶在比赛中丧生,令他产生难以回首的哀恸。
更多跑者则被迫“歇息”了一年——这起悲剧按下了国内越野跑的中止键,许多赛事难以通过审批。一些以参赛赢得奖金为生的“赏金跑者”,在一则则比赛延期、取消的通知中,等待着“黄金时代”重启的希望。
跑者从梦中惊醒
从白银越野赛回到家中,许滢初关了手机,将自己在屋子里关了整整一周。她不敢出门,一出门,心中就止不住地生出害怕。家人送来饭食,她也不想吃。“整个人都是懵的那种状态”。
她总在诘问:“怎么会发生那种事情?”
记忆中的那一天充满凄风冷雨,也充满混乱。她本来只报名参加了21公里的黄河石林短距离越野跑,朋友报名了百公里赛事。然而,临到赛前,朋友受了腰伤,不愿再跑百公里,于是,二人互换了比赛项目。
在退赛前,许滢初一度跑到了女子组第一的位置。她拿着登山杖,仅仅跑出20公里不到,就已经手脚发麻,手臂也抬不起来。大风呼啸,她只有八十来斤,甚至感觉能被风吹动。回顾多年越野跑经历,她确信,过去从未有过这样恶劣的天气。
许滢初记不清自己是怎样从赛道上下来的。黄河石林在这位跑步生涯近20年、曾经入选马拉松国家队的跑者心中留下了恐惧的种子。
“闭关”一周后,朋友们与她聊天,她也出门散心,才让自己的思绪逐渐远离了那片石林。可她意识到,多年来以跑步为生,也没有其他爱好,她没法彻底放弃比赛,也没法远离越野跑。“不可能说,你就不敢去参加那些比赛了,对不对?每个比赛都是那么危险的。”
最开始,她只敢找些小越野赛跑跑,调整状态,“去玩玩去”。跑着跑着,她总会不由自主地思索,这一次比赛,会不会又出现白银时的大风、骤雨乃至冰雹?
她开始习惯于在跑山时多带些补给,多带一件衣服。但在后来,这样的包袱还是变成了某种畏惧。日常跑上山去,天气稍有变化,许滢初就想退缩;比赛里,她也颇有些放不开手脚,“胆量都没有以前大了”。家人不许她再参加长距离、需要过夜的越野跑,觉得那对女生而言太过危险。许滢初也选择了妥协,尽量只去短距离的比赛。
恐惧的种子也播撒到了许多没有参加白银越野赛的跑者心中。原探路者飞越队队员梁晶在白银遇难后,他的教练、IchallengeLab俱乐部创始人魏彪有一种“从梦中惊醒”的感觉,“我们突然意识到,去比赛还有可能会出现生命安全问题”。
梁晶的诸多队友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情绪低落,鲜有参赛。魏彪能察觉到,队员们毕竟相处多年,队友出事,他们总会去联想许多场景,“心理上的恐惧会挺多的”。2021年10月,因为合约到期等原因,飞越队解散,队员们各自奔了不同的队伍。
在越野跑的“黄金时代”,频繁的赛事曾帮许滢初实现了许多梦想。
2015年,28岁的许滢初从云南省队宣告退役。最初,她本可以服从分配,到云南省体校做教练,但这份工作的生存压力让她担忧。如果带不出成绩,只有工资收入,“对于现在这社会消费水平来说,那点工资一年够干啥的?”许滢初说。
她估算过,假如转战户外,努努力,一年下来赚个十几万元不成问题。于是,许滢初抛弃了想象中十年如一日枯燥训练学生的日子,选择全身心投入越野跑与马拉松赛事。
在新冠疫情以前,户外赛事频繁。出身云南鲁甸农村的许滢初一度靠着比赛,一年赚得二十余万元,有时一个月的奖金就超过了五六万元,这是她在体制内时许久才能攒下来的数目。
七年里,许滢初见过了世界,也在户外吃尽了苦头。2017年,她去法国参加一场42公里的越野赛,因为早餐吃了冷食,肠胃不适,比赛时,她在阿尔卑斯山上边跑边吐;2020年广东的一场山地马拉松比赛,她少见地退了赛:前半程冲得太猛了,岭南的酷热让她中了暑。
白银越野赛后,她深觉以人之渺小,很难抗衡自然。退役时担忧的金钱问题,反而没有那么重要了。“我觉得一个人身体好,就是一笔很大的财富。”
如今,许滢初开了一家工作室,也留着省队退役后便开始做的工作——带学生跑圈应对体育考试,带成人跑公路锻炼,偶尔才进进山。但她确信,自己会跑到跑不动为止。
残酷行业里的“另类”退赛者
2022年3月底一个8℃的料峭春夜,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内一处操场跑道上,顾冰脱得只剩下一件短袖。他带着一批北京大学商学院的研究生,又开始了一晚14公里的跑步训练。3个月内,他训练的二十余名研究生,将要参加一场121公里的越野赛。
做教练成为了顾冰的新“兼职”。全职跑者的身份渐渐淡去,他也几乎“在这个行业中消失了”,但他觉得,在白银赛前,跑步依然是他的生活,甚至是他的全部。
打小,顾冰在体校、省队跑障碍跑;进入大学后,他又开始了越野跑。在那个全年也只有十几场越野跑赛事的时代,每月只消在一两场比赛里夺得前三,顾冰就能赚到三千到数万元不等的奖金。有了钱,他豪气地请宿舍里的哥们儿吃饭,点外卖,要8块钱的拉面,再加30元的牛肉。
转折发生在2015年,28岁的顾冰跟腱受伤,医生也给它“判了刑”:要想治疗,必须将其敲断,再重新接上。顾冰担心那会彻底摧毁他的跑步生涯,没敢做手术,跟腱从此成为他完赛的拦路虎。
更多的时候,他察觉到了行业里残酷的味道。过去有选手在越野跑比赛中丧命,他也数次身涉险境。
2017年首届地球之巅极限赛中,西藏阿里地区海拔4600多米的高原上,顾冰刚刚跑出十公里不到,就产生了高原反应,“心如刀割”,又头痛,身体没了前进的力气。玛旁雍错湖旁,他想坐下来,休息一阵。
然而,这一坐,他很久没能站起来。原想等待赛事组织方的汽车,可许久没有踪影,十来只野狗倒是闷着头、耷拉着尾巴,渐渐聚集在他身边。顾冰知道,他不能睡,一睡,“它肯定就给你啃了”。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野狗盯着他,慢慢收拢。顾冰没有力气,狗群一靠近,他就扔石头;扔石头没反应,他便挥舞登山杖驱赶。
狗群见没有机会,兀自散去。然而,时间渐晚,寒意又找上了门。太阳落山不久,顾冰就开始浑身发抖。他意识到,再不离开,他就会被冻死。直到此时,赛事方摄影团队因为遗落了摄影器材的零件,驱车回来找,才发现了顾冰,救了他一命。
那一年里,他连续五次退赛。
2018年,他赴陕西参加秦岭国际越野跑挑战赛。山中大雨瓢泼,雨水顺着衣服兜帽流入,他的身体很快湿透了,顾冰冷得打起了哆嗦。距离补给点一公里多的路,他边抖边走,走了二十多分钟。在30公里的补给点,顾冰对志愿者说,他要退赛。
“下边马上就下坡了,你第一名,退什么赛?”志愿者说道。顾冰没有说话,那时,他自觉心里已经彻底崩溃,恐惧笼罩了他。后来,志愿者给了他一件军大衣,他在小太阳旁烤了将近两个小时,才渐渐缓了过来。
顾冰坦承,他喜欢跑步,但他既不是个勤奋的跑者,也不是个拼命的人。他常和别人说,他很“佛”,“不会那么拼”。白银赛前几年,跑圈曾经将一顶“退赛者”的帽子戴在他头上。最初,顾冰作为运动员的好胜心还对这顶帽子颇为抵触,“之前还经常跟别人怼”,后来也无所谓了。
 顾冰参加2018年香港百公里越野跑比赛。(受访者供图/图)
顾冰参加2018年香港百公里越野跑比赛。(受访者供图/图)
危险常在,步履难停
在西藏、秦岭的那些生死时刻,顾冰“只想着活着下来”:“到那个时候,我觉得一切的金钱跟荣誉对我们来说没有意义。首先得活着,对吧?”那些对比赛获胜、拿冠军的欲望,逐渐被磨平。
也是在那几年里,顾冰开始“折腾”跑步以外的生计。他靠着品牌赞助与卖户外装备小赚了一笔,但又因为投资健身房失败,几个人亏了几百万元。后来,他重返校园,慢悠悠地读起北大的研究生。2019年9月,他动了在大理经营客栈的心思,便跑去大理的一家客栈,与老板喝茶、聊天度日,一待就是十个月,直到客栈在疫情中彻底关门。
折腾得久了,2020年再次回京时,顾冰一度觉得自己已经失去靠体育吃饭的能力,甚至卖起了保险。
然而,跑圈还是惦记着他。白银越野赛那一天,顾冰几乎都在接电话。电话那头,人们劈头盖脸就问:“你在哪?”大家都以为他去参赛了。
那时,他在河北。电话中,顾冰答道:我既然还能和你说话,我就没事。
悲剧发生后的这一年,顾冰想了许多。他意识到,无论是怎样的跑圈“大神”,甚至国家级运动员都会在越野跑比赛中遇到险境,需要做出是否放弃的艰难抉择。“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永远是渺小的,”他说到对生命的敬畏,“真是够不到的,咱就及时下撤,没必要把自己的小命给搭出去,对吧?”
不过,对于常年奔跑的跑者而言,危险常在,步履难停。
一位越野跑者觉得,在白银越野赛的问题上,许多人都是“马后炮”:“有些人说如果他们去的话肯定没事,但是你不是当事人,不知道那个地方的情况。你现在脑子很清楚,但是当你身处一个陌生环境,判断力是容易下降的,并不一定有你躺着敲键盘时的判断力了。”
2019成都龙泉超百公里越野挑战赛冠军郑钧月也觉得:“换我去,我可能也会向前跑,谁知道?”
自诩已是“半职业”跑者的顾冰也难彻底割舍跑步。因为过去没有从业经验,在保险公司干了一个月,顾冰觉得“隔行如隔山”。每天晚上下班,他会去跑上几公里。直到那时,他才发觉,他还是喜欢跑步。
顾冰从保险公司辞职了。他顶着压力重返跑圈,甚至在一场越野赛中拿到了冠军。比赛停滞的这一年里,35岁的顾冰一面兼着教练的工作,一面还有些执念:因为几年来的休养,他受伤的跟腱慢慢恢复了。白银赛后,尽管跑圈内外的朋友都劝他不要再跑了,他还是盘算着第三次参加八百流沙越野赛。
2017、2019年两次参赛,他都没能完赛。之后赛事暂停,第三次参赛成了他不知何日可竟的梦。他始终记得,5年前首次参赛时,他啃着放在补给点的哈密瓜,甜蜜的汁水流过干裂的嘴唇,令他发痛。
顾冰希望有机会再次参赛,给自己一个交代。
“大家简直就是在祈祷”
2022年初,贵州越野跑者张交拿定主意,从全职跑者转为兼职跑者。他再次回到了三年前的起点。彼时,他还在老家经营着养鸡场,一面工作,一面参加越野跑比赛。
由兼职向全职跑者慢慢转型的几年,他的成绩越跑越好,如今却再难支撑起仅靠跑步维生的日子。
“赏金跑者”,跑圈里头这样称呼像张交这样以参加比赛、赢得奖金为生的人。这门生计在新冠疫情暴发前曾扭转无数人的命运。
在接触跑步前,张交身型肥胖,月入不过四五千元。大约从2019年底开始,他专职跑步,当年就拿到了十四万余元的越野跑赛事奖金。
魏彪觉得,疫情以前,越野赛的趋势一度是“越来越好”,原先一年只有十几场,后来暴涨至一年能有几百场,其中也许有几十场设置有奖金。“我觉得行业是趋于成熟、合理,(越野赛)这个概念在循序渐进地发展。”
疫情与白银悲剧却令这一切暂时陷入沉寂。据魏彪观察,目前全国范围内,大型的越野赛依然处于停滞状态。
没有越野赛事,跑者自然也就没有奖金。萨洛蒙国际队队员、越野跑运动员姚妙坦承,她原先一年几十万元的收入要下降大约四成。不过,靠着专业队伍的签约费用与品牌赞助,她维持生活并不算难。
更困难的是没有专业队签约的越野跑“个体户”。贵州跑者赵国虎直言,近两年收入“真的很差”。他在转为专职跑者后,曾经一个月就能跑六七场比赛,而现在他的赛事频次已经降低至一个月一场都不到。2021年,仅靠跑步,赵国虎“基本上没有收入”,不得不在一家健身房兼职做教练。
张交在一两年内就耗光了多年参加越野跑比赛攒下的十万多元积蓄——过年要花钱,家里老人也需要他赡养。2022年上半年,白银悲剧在跑圈掀起的风波稍稍平息,本可参加的一些赛事又因反复的疫情泡了汤。他去了浙江,试图找一份工作,眼下还没能如愿。
无论是出于爱好,还是为了生存,无数跑者都在等待越野跑复苏的信号。河北崇礼成为了他们的牵挂:2022年7月,崇礼168国际超级越野赛将要举办。
2021年,受疫情影响,崇礼越野赛未能如期举办。对于2022年的比赛,一位越野跑教练直言:“大家不光是等着了,简直就是在祈祷和祝福了。”
跑者游培泉已经报名了,在2020年,他夺下了崇礼100公里越野等四项赛事的冠军。他预测,许多跑圈顶尖选手会被崇礼越野赛吸引。已退役的马拉松国家队运动员就曾和他说,“关注度这么高,我是不是也得来跑跑?”
竞争压力陡增,但游培泉反而更加期待。他和圈内朋友一致认为,这场比赛将是越野跑行业能否迎来复苏的风向标,会传达一些信号:“如果崇礼能办,别的地方也有可能。”
(文中许滢初为化名)

 环球产经网
环球产经网